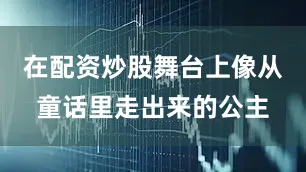荔枝的“两副面孔”
《长安的荔枝》中的荔枝好吃,也不好吃——因为大多数人是吃不到的。杜牧在《过华清宫绝句》中就写得很明白: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驿马踏着尘土疾驰而来,扬起的红尘里藏着数不尽的奔波与耗费,却只换得贵妃唇边一抹浅笑,旁人哪里知晓这风风火火的动静,竟是为了远途而来的荔枝?
不过,岭南的荔枝,大概真可谓人间至味,不然苏轼也不至于在《惠州一绝》中说: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被贬岭南的日子里,一颗颗清甜多汁的荔枝成了慰藉,他索性说要天天吃上三百颗,连归乡的念头都淡了——这哪里是贪嘴,分明是把生活的苦涩,都浸在了荔枝的甘美里。
相对于“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荒诞,更多有关瓜果的古诗词都像苏轼笔下的荔枝,读来满是田园风味,与诗中的景致一起“咀嚼”,叫人口齿生津、回味无穷。
田园间的“果味图鉴”
读范成大的田园诗,好像行走在瓜果飘香的乡间,不经意间就遇见田垄里水灵灵的瓜儿、枝头上明艳艳的果子。
“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(《田园四时杂兴·其七》)这童孙种的是什么瓜呢?冬瓜?黄瓜?南瓜?甜瓜?或者都有。这群乡下小娃娃有模有样地把瓜籽种下去的时候,大概心中的瓜儿已经是成熟的模样了吧。
“梅子金黄杏子肥,麦花雪白菜花稀。”(《田园四时杂兴·其二》)初夏的江南,雨水滋润、阳光慷慨,让各种农作物铆足了劲儿开花、结果、成熟。金黄的梅子争先恐后地从绿叶间探出诱人的笑颜,饱满圆润的杏子在阳光下闪烁着甜酸。
乡野间的瓜果不仅有种植的,还有野生的:“茅针香软渐包茸,蓬藟(lěi)甘酸半染红。采采归来儿女笑,杖头高挂小筠笼。”(《四时田园杂兴·晚春(8)》)其中“茅针”指茅草初生的花苞,剥开其青绿或紫红的叶鞘,露出雪白柔软的穗心。这穗心气味清香,柔嫩微甘,是乡下小孩喜爱的“零食”。“蓬藟”是一种紫红色的果实,其成熟后酸甜可口,同样是乡间儿童的珍爱。你瞧,这些采摘茅针和蓬藟的孩童笑得多开心啊,他们将装满丰收成果的“小筠笼”高高地挑在枝头,相互炫耀着呢。
瓜果里的“弦外之音”
“新霜彻晓报秋深,染尽青林作缬林。惟有橘园风景异,碧丛丛里万黄金。”(《四时田园杂兴·秋日(12)》)这首诗中写的是深秋时节的橘子,在依旧碧绿的叶片丛里,橘子树上却星星点点闪着金色的光芒——这的确是一种“风景异”。每一片叶子都洋溢着生命的活力,而“万黄金”的果子仿佛张扬着丰收的喜庆。
在诗人眼中,橘子不仅好吃,它还是不畏寒霜、意志坚定的象征。屈原的《橘颂》中便有这样的诗句:“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。绿叶素荣,纷其可喜兮。曾枝剡棘,圆果抟兮。青黄杂糅,文章烂兮。”橘树扎根深固难以动摇,所立之志是那么地专一。碧绿的叶子和素洁的花儿相得益彰、缤纷可喜。层层树叶间虽长有刺,果实却结得如此圆润美满,青的黄的错杂相映,色彩灿若霞辉。
你看,一颗果子的滋味竟能串联起如此多的故事与情怀。古人在瓜果香中,品的不仅是果子的味道,还是它们美好的品质。到古诗词里采摘瓜果,真是滋味悠长啊!
来源:《光明少年》2025年8月刊
(文 / 李竹平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教师,语文特级教师,正高级教师,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名师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。)
银利达配资,诺加配资,天津炒股配资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